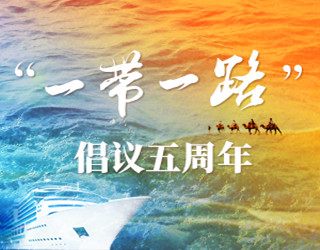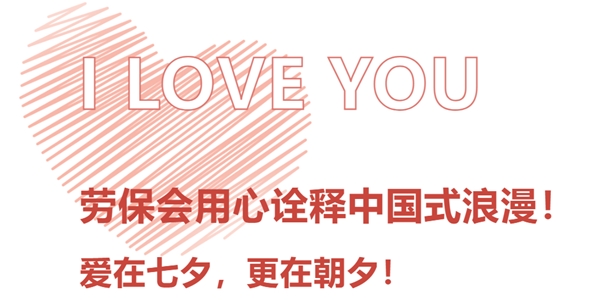我是在寒假的时候去探望萧湖的。或许因为冬的尾音还未褪去,萧湖一如其名,显出萧瑟的样子。
萧湖的水并不清澈,但却让人心生亲切。这不是湛蓝得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的水,也不是被绿藻占领的失去其形的水,它像是乡下老家门前湖泊里的水,诉说着一种原始的野性,一种朴素的自然。我似能在里面听到熟悉的乡音,这是两个不同的生命相互辨认与认同的一种暗号。
因为人少,所以在这里听水,可以直接越过心远地自偏的境界,达到天人合一的层次。水是聪明的,能从远方赶来,拖着疲惫之躯,只为与她赴一面之约的人,值得她托付所有的信任与感恩。虽然来不及把茅草抹上春绿,虽然浑浊的水里泥沙还来不及沉淀,但她秀手一拂,便展开了满湖涟漪;抬头一望,便攫取了一片蓝天白云。即使近处依旧显着泥黄色,但远处已然是波光粼粼,似乎只要再沐浴一番,就会真正连成水天一色。而人也会欣然接受水赠予的美丽。毕竟,水,就是我们来拜访萧湖的原因,也是我们的生命最后的意义形态。
这时,突然想听一首《飞鸟与鱼》。“什么天地啊,四季啊,昼夜啊,什么海天一色、地狱天堂、暮鼓晨钟……”一些想飞而不得飞的思绪,一些如细水呢喃,无法寄形于言语的萌动开始在波光间探出头,你会感到一阵湿润而清爽的喜悦扑面而来,久居陆地的人便在水边得到了一些弥补,一份完善。
在水边,还有一尊吴承恩的雕像,侧卧于阳光下,唐僧师徒四人则沿着一条通天大道,缓缓走入他的梦中。或许,先生创作时所用的墨汁也来源于萧湖之水吧,不然写出的文字里为何总有这熟悉的澹澹水光?我不禁想起《西游记》里那段经典的渔樵对诗,“潮落旋移孤艇去,夜深罢棹歌来。蓑衣残月甚幽哉,宿鸥惊不起,天际彩云开。困卧芦洲无个事,三竿日上还捱。随心尽意自安排,朝臣寒待漏,争似我宽怀?”萧湖,打开了她的子女的胸怀,也为西游世界添上了一抹水声潺潺的想象。难怪赵翼有诗云,“是村仍近郭,有水可无山”。
在公园里沿途还有一些名为“遇见”的木箱,是由淮安区图书馆设立的,里面摆着一排书,时不时就有人前去换一本继续读。我想,枕着萧湖的柔软絮语,翻开一本《西游记》,重新回顾那段取经之路,或许会遇见一些新的惊喜吧。
在一个亭子里,我静静地读着。读着书,读着水,也读着自己。(仇士鹏)
融媒体编辑 潘永勇
 会员投稿
会员投稿 手机版
手机版 |
悦读频道
|
悦读频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