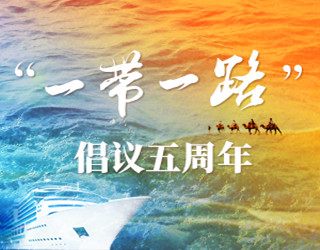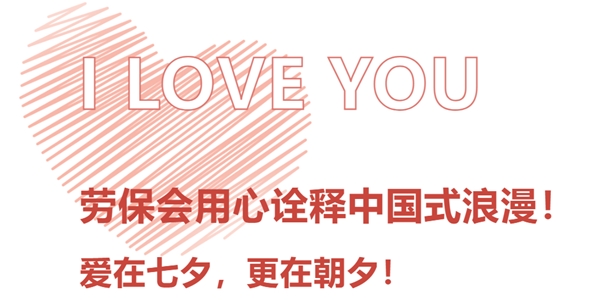周末,母亲又打来电话约我陪她去老家看看。我说:“妈,你老糊涂了吗?老家不是两年前就拆迁了吗?哪里还有房子可看?”电话那头还是那句永不变更的话:“没糊涂呢,老屋拆了,可影子在呢!”
是的,老屋的影子一直都在,在母亲的记忆里,也在我尘封的日记里。
驱车10公里,我和母亲来到正在施工的淮安高铁东站附近,依稀还能辨认出脚下就是我家老屋的原址。下了车,母亲注视着施工现场,想说什么,却若有所思。
在母亲的心里,老屋有她一辈子的期盼和牵挂。老家门前的那条土路,母亲走过70年。母亲在家是老大,姐妹三人,没有兄弟,她是在家招婿的。母亲从出生到老屋拆迁从未离开过那个乡村,三间瓦屋,青砖黛瓦,屋前是一条东西路,我家在西头,路南面是两间锅屋,门前还有一口水井,母亲为了方便左邻右舍一早拿吊筒打水,锅屋门一年四季都不锁。老屋面前有一个清澈的湖,我们村的人都叫它“大洼”,大洼给我的童年留下了太多的美好记忆。大洼周围长满了芦苇、杨树、桑树、柳树。绿柳依依、荷叶田田、芦花摇曳、茅檐映雪,四季的景色渗进了儿时的血脉,伴我一起成长。那时候,到了中午,湖边便热闹起来,洗涤声、淘米声、孩童戏水声、挑夫担水声、邻里谈笑声,在这里交织,整个村庄炊烟袅袅,饭香四溢。当然这洼也是我们儿时的天然“游泳池”。一到夏天,我的小伙伴们就成了“浪里白条”,水性好的,能一口气从洼的这边潜到洼的那边。我胆子小,又被父母看得紧,终究没有在童年学会游泳,这也成了我的憾事。我通常站在岸边帮小伙伴看着衣服,或是捡起一块薄薄的瓦片,弯下身子,让瓦片紧贴水面嗖地一声飞出去,瓦片在湖面划过一道道闪亮的弧线,看着那一圈圈涟漪和被水声惊扰掠水而飞的翠鸟由近而远,整个湖水兴奋了,被笑声淹没……洼边那热闹的笑声和水声就这样响彻了我的童年。
远处,机器正在铺设铁轨,母亲理了理被春风吹乱的白发,笑着说,路比我家房子都高了!
在我的心里,老屋是儿时的万花筒,里面装满了我所有的美好,点亮了我的好奇心。它收藏着我的童年,更收藏着父母一生的辛勤。在这老屋里,父母一手把我们兄妹三人培养成大学生,这在当时的农村,也是屈指可数的,成了十里八乡的佳话。记得小学的时候,家里还没有电灯,母亲为我们准备了煤油灯,因担心我们写作业影响视力,母亲就把灯芯调得大大的。夏天晚上睡觉,躲在棉纱纹帐里,父亲通常先给我们兄妹三人讲一个故事,然后用煤油灯的玻璃罩口紧贴趴着的蚊子,就这样把帐子里的蚊子全部消灭,最后父亲才放心地出来,帮我们按紧蚊帐缝口才回他自己的房间睡觉。老家的蚊子很多,但我们还是喜欢夏天,晚上家家户户屋前放上一张小床,大人小孩人手一把蒲扇,因父母人缘好,村东头的人也都喜欢到我家玩,那场面不亚于开会。你一句他一笑的,好像是在忆苦思甜,又好像是在畅想未来。当然我们最喜欢听邻家的高大爷讲故事,高大爷一辈子没读过书,但他走南闯北信息灵通,成了村里有名的故事大王,讲得可好了,声情并茂。从《西游记》到《聊斋》,从《红日》到安徽小岗村大包干,从讨饭度日到万元户,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滋润了我们幼小的心田,也激发了小伙伴们对外面世界的向往。高大爷还有另一个技能——会替人治“腮腺炎”,我记得我小时候,有一天早上起床后,一边的耳后突然肿起来了,酸酸的,母亲让我去找高大爷,高大爷找来毛笔和黑墨水,在我耳边就这样描啊描啊,最终描成了一个黑太阳,这个黑太阳可神奇了,过几天,耳边的肿块就消了,吃饭也香了,当时我觉得高大爷真是神医呢。
母亲说,外公是没有住过瓦屋的,母亲小时候家里是三间茅草屋,又小又矮。一到梅雨季节,外面下大雨,家里下小雨,至今还记得我拿着盆子和妈妈一起等雨的样子。外公垒了一个土墙院子,院子里长满了一种叫做“节节高”的花儿,当时我也只有四五岁吧,只模糊记得花的颜色是粉的,很好看,母亲说外公很喜欢这花,很像外公要强的性格,他希望每一天的日子都能节节高。外公很会种庄稼,一到夏天,院子里堆满了西瓜,第二天早上,外公在那木头做的“轿轮车”(只有一个轮子)上散放一张柳扁子,再铺几层稻草,然后装上一车的西瓜步行去城里卖。非农忙时,外公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,在外公的心里,那老屋是全家人赖以栖息的处所。累了,外公总会叼起他那长长的旱烟袋,吸上几口烟,带领我们兄妹在院子里转上几圈,含饴弄孙成了外公晚年最幸福的事。老屋只要上不漏,下不倒,外公就会很满足,家也就有了生机、有了希望。母亲每次说到此处,眼睛里就会闪着泪光,我知道,她一定又想起分田到户后第一个丰收的季节,那天外公因脑溢血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第二年,父母便建起了新屋。
我和母亲站在老屋的影子里,母亲自言自语地说:“嗯,再也看不到左邻右舍,一个个晨起,下地劳作的样子了……”,是啊,邻居们都被安置住进了高楼,有了新的生活,老屋的周边已是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高铁路网,家乡也成了高铁枢纽。徐宿淮盐、连淮扬镇、宁淮、京沪二线高铁将从老屋的脚下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延伸着,延伸着……
不知何时,我们身边停了几辆私家车,一群年轻人指着拔地而起的高铁东站,兴奋地高呼:淮安高铁时代来了!
母亲突然面向我认真地问:“景真,你说这高铁通哪儿的啊?”我说:“妈,这您不知道啊,今年年底就通向北京了,明年您就可以乘高铁去看望在上海工作的宝贝孙女了!”母亲听完,微笑地点了点头,脸上的皱纹如同这脚下的路,无限延伸…… (高景真)
 会员投稿
会员投稿 手机版
手机版 |
悦读频道
|
悦读频道